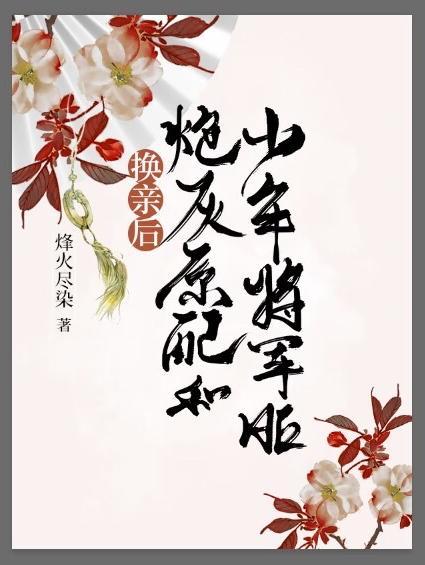纳兰小说>繁霜 番外 > 第22章(第2页)
第22章(第2页)
到了临睡之际,为免得某人起疑心,千芮交待:
“奴婢知道小相爷今日心情不畅,因此浴汤和熏香中都换了静心安神的药材,与往日用的略有不同。”
初春的寒气依然沁人,千芮把手伸进被窝,感温度合宜,又转身告诉他:
“对了,被窝也是用可安神的热石烫暖的。”
“小相爷好好睡一觉吧。”千芮柔声交待,凌云洲不说话,她正欲退下不扰他清净。
“站住。”
他坐在榻上,抚着额,略显疲惫,懒懒将她叫住。
从来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揣测他的心思,身边的人对他精心照料,极尽讨好,但也从来没有哪个奴婢会亲自把手伸进他的被子里,去为他感受被子温度合宜。
“你怎么敢肯定,我今天心情不畅?”
他语气严肃,想着今日她在灵堂上对凌夫人说的那些话,看似在替他出气,但她分明是想为别人求情。
今日发生过那么大的事,就连旬邑和窦管家都默默地离他远点,少跟他说话,虽然他确实心情不畅,但他一向不允许轻易被人看中说中。
“别生气,奴婢不敢。”
好没意思的跪地求饶。父相自幼教导,谋事者,喜怒不形于色,被看穿喜怒哀乐是愚蠢和懦弱的行为。
“又如何看出,我生气了?”
他语气严肃,表情却慵懒,把脚伸进暖烘烘的被子里,倚靠在榻上,千芮倒也不真的怕他。
“今日之事,就是小相爷想让我看的笑话吗?”
凌云洲伸手抓住她,用了些力道攥着,质问:
“你为他们求情,”他抬眼讥笑看她:“你忘了你摔下山有多疼了吗?”
“我没忘,可那是你年幼时真心当成母亲的人。”
“那又如何?”他捏着她手腕的力度加大:“都是虚情假意。”
“我从不认为,这世间所有父母都真心爱他们的子女。”千芮看着凌云洲,她很认真地说:
“我也从来不认为,父母就一定是对的那一方。”
“窦管家跟我说过,小相爷年幼时,整日粘着凌夫人,她也曾真心待你,直到有了云玺公子,你才被送走,每个人年幼之时最依恋的,莫过于母亲,在你内心深处,对她有母子之情。”
他抬眼看她,目光猩红,她真的敢揣度他的心思,说如此忌讳的话。
“若真的杀了凌夫人,你心里会很难过吧,否则,你不会在山谷耽误那么多天,你是想看看,她究竟会做到什么程度吧。”
“没想到,你这么会揣度别人的心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