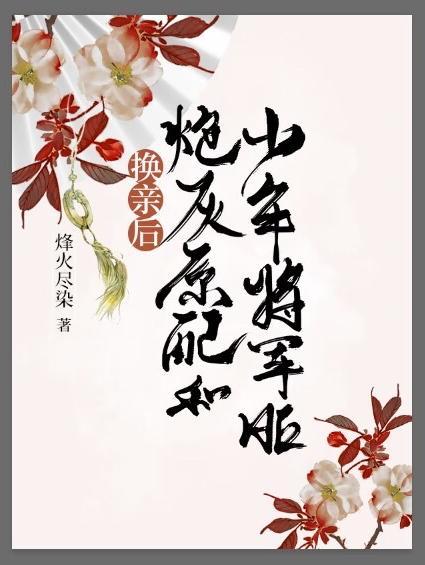纳兰小说>菡萏记山中君 > 7080(第13页)
7080(第13页)
空气里浮动着玫瑰香,还有血腥气。
姜菡萏鼻子有一点酸——他那么灵的鼻子,竟然没有闻出血腥气不是她的,而是他自己的。
她从枕下摸出火折子,轻轻一吹。
光亮像水一样盈满室内,黑暗被驱散。
阿夜回头,看到那一团的火光映照着姜菡萏的脸,她的脸像是在业火中绽放的圣莲。
这一幕和多年前在丹房那一幕重叠,那时他还不会说话,没有人把他当人看,包括他自己,只以为自己是狼。
是她教会他用火折子,是她教会他说话,是她教会他如何当一个人。
她就是他唯一的神。
而此刻,她的衣衫凌乱,脖颈上还留下了掐痕,她的眼中含着一层薄薄的泪光,在他回头的那一瞬,泪水落下来。
她终于看清了他的伤势,除了肩头留下的枪伤,他的后背共有三处箭伤,鲜血已经浸透了黑衣。
她早该想到的,他再厉害也是个人,那样的箭雨没有任何人能全身而退。
她的泪珠划过火光,晶莹如叶上露,天上星。
阿夜整个人晃了晃,双膝落地,跪在她的面前。
他……做了什么?
他对她做了什么?!
自从救回阿夜,金创药就成了姜菡萏身边必备的东西,她点上灯,迅速找到药,很有经验地把衣料剪开,露出底下的箭簇。
这箭簇和她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,它更加狭长、尖利,倒钩已经陷进去一半,若是像之前那样徒手往外拔,势必会带来更严重的外伤。
就在这个时候,阿夜伸手摸到了外面那截剩下的箭杆。
“不行,不能拔,一定得找——”
“大夫”两个字还在喉咙里,姜菡萏就看见阿夜的手用力——用力把整个箭簇按进身体里!
姜菡萏忍不住尖叫。
阿夜全身的皮肤都因这一下而沁出一层薄汗,黑发漉湿。
他低声喘息,手伸向第二支。
姜菡萏抓住他手:“你疯了吗?!”
“这是我该得的。”阿夜看着她,脸色苍白如死,黑发与黑眸浓深如黑夜,“菡萏,我这样对你,我该死。”
即使是失血中的阿夜,力量也不是姜菡萏能抗衡的。哪怕姜菡萏用尽全力,他的手还是一寸寸接近第二支箭簇。
“笨蛋,笨蛋!”姜菡萏眼中急出了眼泪,“你知道错了,你就改啊!你放我出去不就好了吗?!”
第二支箭簇深陷进血肉中,血流如注,沿着被汗水打湿的背脊一直渗进地面的红茸毯中。
阿夜全身绷紧,无声地仰起头。
良久,他低下头看着姜菡萏:“我做不到……菡萏,你杀了我吧,我死了,就不会再拦着你了。”
疯子!这个疯子!
姜菡萏仆上去抱住他的手,在他握住箭簇时重重咬在他的手掌上。可第三支箭簇还是一点点扎了进去。她嘴里尝到腥甜的滋味,不知道是她咬出来的血,还是他伤口流出来的血。
她的泪水止也止不住,泪混着血,又苦又腥又咸。
“菡萏……看到了吗?刀在那儿。”阿夜已经无力抬头,只能用视线告诉她。
刀在楼梯口,他上楼时随手扔在一旁。
“拿过来……杀了我……”阿夜低着头,声音很低,“杀了我,你就自由了……”
这句话说完,他摇摇欲坠的身体终于倒下。
“笨蛋,笨蛋,笨蛋!”
姜菡萏从来没有这样恨过,也从来没有这样哭过。酸甜苦辣在胸膛里揉作一堆,心脏好像已经被揉碎了。
*
严何之最近天天来找李思政下棋。
李思政本就勤勉,每天都在官署中待天黑,这些天更是直接待到深夜,两人才离开官署,各自归家。
他们在等。
无论是澹园还是庆州,人们对阿夜的忠诚崇拜都超乎想象。若是计划成功,小姐离开,断了线索,他们也许还能保住小命。可是现在计划失败,小姐被带回澹园,在阿夜的威压之下,没有人能扛得出不招认。
澹园安静,是因为阿夜这些天在养伤。
等到阿夜养好了伤,就是向他们清算的时候。
这日是两人下棋的时候,林知春向他们送来园中最后一茬柚子。
中秋和重阳都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了,风中的寒意越来越深,经霜的柚子最甜,两人却是食不知味。
“二位为何会相助姜小姐?”林知春开门见山地问,“陛下垂危,太子年幼,天下正需要一位强主。而天下最强的人莫过于夜统领。若是娶了姜家嫡女,夜统领便可以得到半璧江山,到时一统天下,指日可待。二位都是人杰,为何偏要与夜统领作对?”
李思政与严何之久在庆州,深知林大任能有今日,皆是林知春在背后筹谋。两人叹了口气,李思政道:“知遇之恩,不能不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