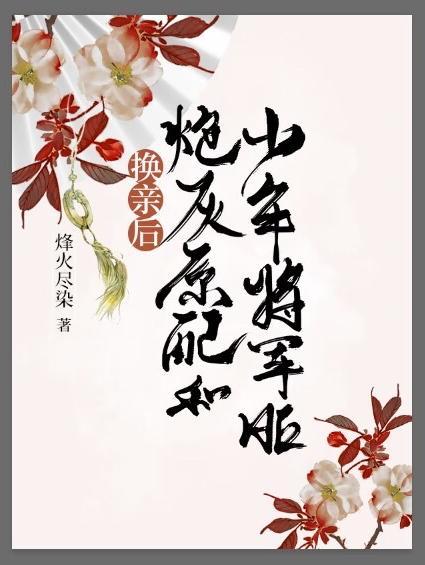纳兰小说>繁霜鬓怎么读 > 第36章(第1页)
第36章(第1页)
她积蓄了所有仅剩的力气刺去的竹刺扑了空,她转头,满眼噙着杀气。
是凌云洲,他来了。
然儿侍女看到凌云洲,立刻齐齐下跪,最强壮的那个,扶着自家小姐,看凌云洲脸色严肃,带着哭调说道:
“小相爷,我为我家小姐寻前日遗失的绒花,”
然儿侍女怯生生看了千芮一眼,“奴婢看到姑娘头上别着,便上前询问,不曾想,这、这人不知为何,竟与然儿小姐打斗起来——”
然儿侍女将“罪证”递上,继续说:
“这绒花工艺复杂、价值不菲,是我家小姐特地命人打制的,都城里不会有第二支。”
千芮听了然儿侍女的话,她踉跄地要站起来,跌倒,凌云洲立刻拢住她的腰,扶住。
她狼狈不堪,脸上污浊青肿,嘴角流着鲜血,头发凌乱,衣服上沾了黏黏的血迹,手背上,也都一片血肉模糊,凌云洲心里腾起一股怒火。
凌云洲低头,旬邑将侍女的绒花拿过来,交给他,他将两只绒花放在手中仔细端详,鹅黄色的花蕊精巧漂亮,确实是上品。
“这绒花价值多少?”
“十两!”千芮轻声说,然儿侍女同时大声回答:
“足足百金!”
“绒花已坏,相府改日会奉还更精致的发簪,”
凌云洲看着千芮,她脸色惨白,脸上都是污泥,眼框发红,没有流泪,她立不稳,却努力地让自己立住,尽力让自己不倚靠在他身上。
然儿轻轻拭泪,看着凌云洲,声音柔弱胆怯:
“怎能劳烦小相爷,这绒花发簪,这位妹妹若喜欢,当我送给这位妹妹的吧。”
只见凌云洲面色冰冷,不知道这话是向着谁说的:
“人应该自知,不该拥有与自己不匹配的东西,今日之事,相府自会给你们一个说法。”
几个侍女听得此话,像看一只落水狗一样看千芮,嘴角都压不住笑意,把哭成泪人的小姐扶了走了。
千芮怔怔地盯着然儿侍女离去的方向,她嘴角,也噙着一丝微笑,一丝绝望的微笑,只觉得天旋地转,脚下像踩在了棉花上虚软无力。
好疼啊,这算什么无妄之灾?
千芮心里冒出一句脏话:
真他娘的疼。
不知道为什么,身上的伤,疼得麻了,似乎变得毫无痛感,只是她的心,也开始绞着疼,已经够悲惨落魄了,她不懂为什么自己这颗心还要让她痛。
她希望他没来,或者晚来那么一瞬间。
如果那样的话,她应该已经死在然儿的毒针下,只不过那然儿也未必能活。
她一个女奴,与那披着假面皮的什么小姐贵人同归于尽,这笔账划算。